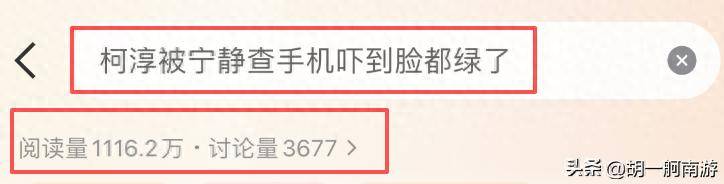10月18日,第十二届乌镇戏剧节的小镇对话现场,饶晓志导演与演员陈明昊、尹昉、杨超越围坐一堂,以“舞台银屏,双向奔赴,多重收获”为主题展开了一场轻松又深刻的对谈。从戏剧新人的舞台初体验,到资深创作者对舞台与银屏两种表演形式的比较和思考,还有AI时代戏剧的独特价值,四位嘉宾真诚分享自己的经历和感受。

陈明昊、尹昉、杨超越、饶晓志(从左至右)在乌镇戏剧节参加小镇对话
戏剧新人收获意外的自由
作为嘉宾中最年轻的“戏剧新人”,杨超越的舞台初体验成为开场焦点。去年她因饶晓志导演邀约加盟话剧《你好,疯子》,这位习惯了影视镜头的演员,第一次感受到“从唱变成说”的差异——舞台表演的连贯性与重复性,让她在不同场次的同一剧情节点,触摸到表演的多元可能。“影视拍摄会暂停,但舞台上的每一次重复都有新感受,这就是它的魅力。”
谈及初登舞台的压力,杨超越直言“每天上场都怕卡词”,曾有一次“心里咯噔一下”,却凭着临场反应“不表现出来”。而这段经历也让她收获了意外的自由:“影视镜头里做动作会被说‘抢戏’,动作幅度、演员站位都有限制,但舞台上没有这些束缚,我更敢调动肢体了。”从被动等待剧情“按开关”,到主动寻找身体与角色的连接,舞台成为她突破表演边界的新出口,在看完乌镇戏剧节开幕大戏《人类之城》中德国女演员酣畅淋漓的独角戏之后,她甚至表示:“也想试试一个人在台上‘发疯’,突破自己的极限。”

杨超越畅谈“戏剧新人”体验
舞台练“根”,银屏练“准”
对于陈明昊、尹昉、饶晓志三位“双栖”创作者而言,舞台与银屏的表演差异,从来不是“技巧优劣”的二元对立,而是有着“生长土壤”与“呈现逻辑”的本质区别。
陈明昊用“鲜活的生命体”比喻演员:“表演不是技巧,是身体直接地表达。舞台和影视是不同土壤里长出来的东西,观众看到的不是道理或故事,而是感受。”他以自身经历举例,影视拍摄常聚焦“上半身表演”,甚至“拍聊天的戏时,可以下半身盖着军大衣,只演上半身”,但舞台上“观众的镜头由自己决定”,强调身体整体的表达力。

陈明昊和尹昉分析影视和戏剧表演差异
舞者出身的尹昉,认为舞台对身体的开发让他在影视中更懂得“挖掘局限”:“从小对身体的认知,让我知道角色的呈现往往需要暴露弱点,而身体是所有表达的起点。”他从“载体与本质”的角度切入:“舞台的‘在场性’是现场的呼吸与互动,影视则通过剪辑二次呈现。”舞台排练是“不断试错、寻找可能性”,而影视拍摄需要“快速进入状态,更直接地抵达目的”。
杨超越表示在舞台上找到了影视表演的“能量补充”:“舞台上的肢体放开后,再回到影视镜头前,我更清楚如何‘收放自如’,不再害怕动作‘抢戏’,而是懂得用身体传递情绪。”
陈明昊的总结更为直白:“影视是工业流程,需要清晰的目标和高效的合作;戏剧是手工作坊,允许未知与探索。演影视时盼着收工,演戏剧时等着‘找到感觉’——这两种状态让演员始终保持对表演的新鲜感。”
饶晓志作为戏剧和影视双栖导演,更能体会两种创作的不同快感:“戏剧导演在控台后感受全场的笑声与呼吸,那种即时性的节奏共鸣,和电影后期剪辑时的精细调整,是完全不同的满足。”

饶晓志作为戏剧和影视双栖导演分享体会
AI时代,用戏剧的“在场性”抵抗虚拟
当对话谈及AI对表演行业的影响,四位嘉宾给出了一致的乐观——戏剧的“在场性”,是AI难以替代的核心。
尹昉提到此前在国际舞蹈节的讨论:“AI能替代电影剪辑、作曲、设计,但剧场的现场发生、人与人的面对面互动,很难被数字化和算法渗透。这不是戏剧的‘落后’,而是守住了人类实体存在的底线。”
陈明昊认为:“世界本来就是新事物替代旧事物,但戏剧的本质是‘人站在舞台上,让时间从身体经过’,这种最朴素的存在方式,AI复制不了。”
杨超越笑言:“如果AI真那么厉害,我就回去干活。”
饶晓志则点出关键:“AI让我们更懂得‘何为人’,而戏剧一直在讨论人本身——当屏幕无处不在,剧场里人与人的汇聚,反而更显珍贵。”

陈明昊、尹昉、杨超越、饶晓志(从左至右)在乌镇戏剧节参加小镇对话
对话最后,面对观众关于“青年戏剧人如何坚持”“新手该看什么戏”的提问,嘉宾们都给予了真诚的回答。杨超越说“能坚持热爱的事很幸福,热爱的样子值得被看见”;尹昉直言“青年人不需要建议,要自己试错,错了就改,没错就一条路走到黑”;陈明昊则强调“戏剧是提问题,不是给答案,能让观众产生思考的,就是好戏”。
这场关于舞台与银屏的讨论,最终指向的也不是表演形式的分野,而是对“人”的探索——无论是在舞台上释放肢体,还是在镜头前捕捉微表情,表演的本质永远是“真诚”,而双向奔赴的意义,就是在不同的载体里,始终保持对艺术的热爱与好奇。
来源:北京日报客户端
记者:王润