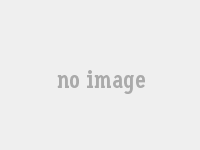“你听说了吗?王家村那个……”
“哪个?”
“还能哪个,就那个犟老头。”
“他那三轮车,响得跟拖拉机似的,今早没声了。”
01
王家村缩在青峰山脚下,像块被日子磨旧了的土布。天还没亮透,一层薄薄的灰雾贴着地面,王建国就起来了。

他屋里的光是灶膛里跳出来的,一闪一闪,把他的影子拖得老长,印在斑驳的土墙上。
他往锅里添了瓢冷水,水气“刺啦”一声,雾气更浓了。
他从篮子里摸出两个鸡蛋,在锅沿上磕了磕,蛋液滑进滚水,很快凝成两团嫩黄的荷包蛋。
孙子小远就坐在灶门前的小板凳上,一声不吭地看着火,火光映在他脸上,那张脸总是带着点儿捉摸不定的笑,像是看到了什么别人看不见的东西。
王建国把荷包蛋捞进豁了口的瓷碗里,推到小远面前,碗边烫,他没说话,只是用眼神示意孙子慢点吃。
小远用勺子笨拙地戳着蛋黄,橙红色的蛋汁流出来,混着热气,是这间屋子里最鲜活的颜色。
三年前,小远的娘,也就是王建国的儿媳,得肺病走了,留下这么个脑子有点不灵光的孙子。
王建国没掉过几滴泪,只是把儿媳的丧葬费换成了三十只芦花鸡,在后山搭了个鸡棚。
他觉得人走了,日子还得往下过,小远不能断了药,也不能不去村小的特殊班。
喂完小远,王建国就挑着担子去后山。鸡棚里那股混着鸡粪和草料的味道,他闻了三年,早习惯了。
鸡看见他,扑棱着翅膀围过来,咯咯咯地叫。
他把拌好的糠撒在地上,然后钻进鸡窝里捡蛋。
鸡蛋摸上去还是温的,有的上面还沾着新鲜的鸡粪和草屑。
他把蛋一个个码进筐里,心里默数着,今天收成不错,有二十多个。
这些蛋是他的指望,是小远的药钱和学费。
他这人,犟了一辈子,认死理,觉得人只要凭力气吃饭,就不该有啥过不去的坎。
村里谁家拖拉机坏了,水管漏了,他去帮忙,弄得满身油污,从不要一分钱。
可一提到小远,他那张被风霜刻出褶子的脸就绷不住,那是他身上最软的一块肉。
每周三和周六,是王建国进城的日子。
他那辆旧三轮摩托车是家里唯一的大家当,还是媳妇没病倒前,两人一起去镇上买的。
发动起来的时候,整个车身都在抖,排气管“突突突”地吼,像个得了哮喘的老头。
他把两筐鸡蛋用草绳捆在车后座上,盖上块洗得发白的旧蓝布,然后把小远抱上车,让他坐在自己身前,用身体护着。
城里的早市在一条老街上,天刚亮就挤满了人。
王建国把三轮车停在老地方,一个不起眼的墙角。
他把鸡蛋摆出来,也不吆喝,就坐在小马扎上抽烟。
老主顾们认得他,也认得他的蛋。
一个烫着卷发的大婶过来,挑了十个蛋,说:
“老王,你这蛋好,蛋黄红,我孙子就爱吃你家的。”
王建过接过钱,又从筐里多拿了一个递过去:
“孩子吃,不算钱。”
邻摊卖菜的张婶凑过来,压低声音说:
“建国啊,你听说了没?最近查得严,说卖东西得有啥证。你这鸡蛋,可别被他们撞上了。”
王建国把烟蒂在地上摁灭,浑不在意地摆摆手:
“我自己家鸡下的蛋,又不是偷的抢的,要啥证?”
“他们还能管天上的鸟下蛋不成?”
02
那天收摊早,他还剩下十几个蛋。

一个瘦高的女人领着个小女孩,在他摊子前站了半天。
王建国认得她,是住在附近小区的李姐,一个人带孩子,不容易。
李姐挑了几个蛋,掏钱的时候有点犹豫。
王建国把剩下的蛋都装进一个布袋里,塞到她手里:
“拿着吧,孩子正长身体,多补补。”
李姐愣住了,非要给钱,王建国已经发动了三轮车,在一阵浓烟和“突突”声中走了,只留下一句:
“下次再说。”
他觉得心里舒坦,能帮一把是一把,就像当年村里人帮他盖房子一样。
那个周五,天阴沉沉的,像是要下雨。
王建国照常出摊,刚把第一筐鸡蛋摆好,两个穿着蓝色制服的人就走了过来。
那制服很挺括,跟早市里这些卖菜卖鱼的人显得格格不入。
其中一个高个子指着他的摊子,声音没什么温度:
“老乡,你这是无证经营农产品,知道吗?”
王建国愣住了,他抬起头,眯着眼打量着对方。
他卖了三年蛋,头一回听见“无证经营”这几个字。
他站起来,拍了拍裤子上的灰:
“同志,啥叫无证经营?”
“我这是自己家养的鸡下的蛋,卖点钱给孙子买药。”
“自己家养的也要证。”
另一个矮个子的很不耐烦,“规定就是规定。赶紧收了,下次再让我们看见,就要处罚了。”
“罚……罚款?”
王建国觉得这事有点荒唐,“我卖个蛋,犯了哪条法了?”
“跟你说不通。”
高个子不想多费口舌,“要么你自己收,要么我们帮你收。”
他说着,作势要去动王建国的鸡蛋筐。
王建国急了,一把护住筐子。
周围的摊主都围了过来,张婶在旁边小声劝他:
“建国,算了算了,别跟他们犟,先回家吧。”
“是啊老王,好汉不吃眼前亏。”
王建国看着那两张面无表情的脸,又看看周围人劝诫的眼神,心里的那股气像是被一盆冷水浇灭了。
他没再说话,默默地把鸡蛋一个个收回筐里,解开绳子,推着三轮车往回走。
车子没发动,他推着,那沉重的车身就像他此刻的心情。
一路上,他脑子里都在嗡嗡作响,啥是证?
这证,到底要去哪里办?
他想不通,回家对着小远也提不起精神。
小远似乎感觉到了什么,那天格外安静,自己拿着小人书,翻来覆去地看。
周一,王建国起了个大早。
他没去喂鸡,而是从床底下那个带锁的木箱子里,翻出家里所有的积蓄,一共五百三十二块钱。
他数了三遍,抽出五百,塞进内衣的口袋里,用别针别好。
他要进城,去办那个“证”。
他觉得,只要是官家说的,总有个地方能办。
03
他骑着三轮车去了镇上的政务大厅。
那地方又大又亮,地板滑得能照出人影,跟他那泥土夯实的院子是两个世界。
他走到一个挂着“综合窗口”牌子的地方,排了半天队,轮到他时,他小心翼翼地问那个戴眼镜的年轻姑娘:
“同志,俺想问问,卖自己家的土鸡蛋,要办个啥证?”

姑娘从一堆文件里抬起头,看了他一眼,然后递给他一张宣传单:
“喏,自己看。”
“要先去工商所办营业执照,再去市场监管局办食品经营许可证,卖农产品的话,最好还要有农产品检测报告。”
王建国拿着那张纸,上面的字他认得七七八八,但连在一起就看不懂了。
他只听懂了“检测报告”几个字,又问:
“那……那这个检测,要去哪里弄?”
“先去村里开个证明,证明你家确实养了鸡,然后去县里的农检中心做检测。”
姑娘说着,又补充了一句,“一套流程下来,快的话也得一个月。检测费大概两百多。”
一个月?
还要两百多?
王建国脑子“嗡”的一声。
他就三十只鸡,一天下二十多个蛋,全卖了也就百十来块钱。
等一个月,小远的药早就断了。
他急了,把那张纸递回去,声音带着点恳求:
“同志,俺……俺不是开店做大生意的,就是自己家那几只鸡,能不能通融一下?”
“不办行不行?”
姑娘摇摇头,公式化地回答:
“规定就是这样,我们也没办法。”
“现在食品安全抓得严,没证就是不能卖。”
王建国还想说什么,后面排队的人已经不耐烦地催促起来。
他只好拿着那张没用的宣传单,失魂落魄地走出了政务大厅。
外面太阳很大,照得他眼花。
他骑上三轮车,那“突突”的声音此刻听起来格外刺耳,像是在嘲笑他的无能。
回到家,天已经快黑了。
他推开门,看到小远正坐在门槛上等他。
王建国走过去,摸了摸孙子的头,一句话也说不出来。
晚饭后,他习惯性地去拿小远的药,才发现药盒已经空了。
那药是进口的,一盒一百八十块,只能吃半个月。
他想起口袋里那五百块钱,又想起抽屉里剩下的三百二十块。
这个月要是再卖不成蛋,下个月小远的学费也没着落了。
夜里,王建国睡不着,一个人坐在鸡棚旁边的石头上抽烟。
月光把他的影子拉得很长。
鸡棚里,芦花鸡在安静地打盹,鸡窝里静静地躺着一窝新下的蛋。
他看着那些圆滚滚的鸡蛋,心里又急又气。

烟一根接一根地抽,火星在黑暗中明灭。
他不卖蛋,小远怎么办?
可要去卖,那个“证”就像一座大山,压得他喘不过气。
他想不明白,为什么自己辛辛苦苦养鸡下蛋,到头来却连条活路都没有了。
人被逼到绝路上,胆子就大了。
王建国决定再去一次,就一次。
他想,我去得早一点,找个更偏僻的角落,卖够小远的一盒药钱就走。
周三的凌晨,天还是黑的,王建国就骑着三轮车上路了。
他绕开了人多的大街,从一条没人走的小巷子穿过去,在早市最末端的一个垃圾站旁边停了下来。
这里气味难闻,几乎没人过来。
他把鸡蛋摆好,心里像揣了个兔子,七上八下的。
一个早起锻炼的老大爷路过,买了他八个蛋。
王建国收了钱,心里刚松了口气,一抬头,就看到那两个熟悉的蓝色制服又朝他走来。
04
这一次,他们身后还跟了一个人,手里拿着相机。
王建国的心一下子沉到了底。
“又是你。”
高个子制服冷冷地说,“跟你说过了,不准卖,怎么还来?”
“我……”
王建国刚想解释,那个拿相机的人已经对着他的摊子和他的人“咔嚓”“咔嚓”拍了好几张照片。
闪光灯刺得他眼睛发花。
随后,矮个子制服从包里拿出一张纸,递到他面前。
王建国接过来,看到上面印着一行黑体大字:“行政处罚决定书”。
他看不懂那些密密麻麻的小字,只看到了最下面那个用阿拉伯数字写的金额:20000。
“两……两万?”

他以为自己眼花了,用粗糙的手指又数了一遍那串零,没错,是两万。
他的手开始抖,那张轻飘飘的纸,此刻却重如千斤。
他抬起头,声音都变了调:
“同志,你们是不是搞错了?”
“我这一整筐蛋,全卖了也就一百二十块钱,你们罚我两万?”
“没错,就是两万。”
高个子指着上面的条款,“根据《食品安全法》规定,无证经营,货值金额不足一万元的,处五万元以上十万元以下罚款。考虑到你是初犯,又是弱势群体,我们已经申请了从轻处罚,只罚两万。”
他说得理直气壮,好像这两万块钱是一种恩赐。
“我没钱!”
王建国喊了出来,“我一分钱都没有!”
“没钱?”
矮个子冷笑一声,“没钱就扣你的车。你要是再不配合,我们就去法院申请强制执行,到时候封你的房子!”
“扑通”一声,王建国跪下了。

他活了六十二年,没跪过天,没跪过地,此刻却跪在了这两个比他儿子还年轻的人面前。
他抓住高个子的裤腿,老泪纵横:
“同志,求求你们,行行好。”
“我孙子有病,等着钱买药,我真没钱啊。你们少罚点,罚我一百、两百都行,我认了!”
周围渐渐围上了一些人。
买他蛋的李姐正好路过,看到这一幕,也赶紧过来求情:
“是啊,两位同志,他家情况是真困难,就靠这点鸡蛋钱过日子,家里还有个生病的孩子,你们就通融通融吧。”
“我们也是按规定办事。”
高个子把王建国从地上扶起来,但脸上没有丝毫动容,“你要是不服,可以去申请行政复议。别在这里妨碍我们工作。”
说完,他们不再理会王建国的哀求,其中一人径直走到三轮车旁,推着车就要走。
王建国想去拦,被另一个人挡住了。
他就眼睁睁地看着自己那辆破旧的三轮车,那辆载着他和孙子、载着全家希望的三轮车,被推走了。
他一个人瘫坐在冰冷的地上,手里死死地攥着那张两万元的罚单,眼泪止不住地往下流。
周围的人指指点点,有同情的,有叹息的,但没人能帮他。
05
早市的喧嚣声还在继续,可那些声音都离他很远,他什么也听不见,只觉得天塌了。
王建国不知道自己是怎么从地上爬起来的。
他像个游魂一样,在街上慢慢地走。
路过药店时,他停下脚步,隔着玻璃橱窗,看到了里面摆放着的那种他再熟悉不过的药盒。
小远早上出门前还拉着他的手说:“爷爷,我想走路,不想一直坐着。”
那句话像一把刀,在他心口上反复地割。
回到家,院子里空荡荡的,往日停着三轮车的地方,只剩下一片压实的泥土。
那辆车是媳妇生前,两人省吃俭用几个月才买下的,是这个家唯一的交通工具,也是他对妻子最后的念想。
现在,没了。
他走进屋,拉开那个破旧的抽屉,里面有一把生了锈的水果刀。
他把刀拿在手里,冰冷的铁器贴着掌心。
他觉得自己太没用了,连孙子的药都买不起,连卖几个鸡蛋养家糊口的权利都没有。
活着,还有什么意思?
可他一转头,看到了墙上贴着的小远用蜡笔画的画,画上一个老头牵着一个小男孩,旁边是几只咯咯叫的鸡。
他要是走了,小远怎么办?
王建国把刀扔回抽屉,眼神却变了,那双浑浊的眼睛里,有什么东西正在燃烧,越来越旺。
他站起身,走到后山鸡棚,把鸡窝里剩下的所有鸡蛋都装进一个蛇皮袋里。
然后,他锁上鸡棚的门,也锁上了自家的门,提着那袋鸡蛋,朝着镇上“市场监督管理大队”的方向走去。

路上遇到村里人问他去哪,他也不答话,只是埋着头,走得越来越快。
他心里只有一个念头:我要我的三轮车,我要去问问他们,卖几个自己家鸡下的蛋,到底还要什么证?
市场监督管理大队的院子很大,门口停着几辆执法车。
王建国一眼就看到了自己那辆破旧的三轮摩托,它被孤零零地扔在院子的角落里,像一件被人丢弃的垃圾。
他提着鸡蛋,疯了一样冲过去,想把自己的车推走。
门口的保安拦住了他:
“哎哎哎,你干什么的?”
“这里不能随便进!”
王建国一把推开保安,吼道:
“那我的车!”
保安伸手去拽他,两人拉扯起来。
就在这时,王建国眼角的余光瞥见旁边停着一辆没熄火的电动三轮车,钥匙还插在上面,应该是哪个工作人员临时停靠的。
他脑子里“轰”的一声,像是有一根弦彻底断了。
他甩开保安,一个箭步冲过去,跨上那辆电动三轮车,拧动了油门。

车子猛地向前窜了出去。
而里面正谈笑风生的矮个子工作人员无意中抬头,看到了正在加速冲来的车。
那一瞬间,他的眼睛睁得如铜铃般大,瞳孔急剧收缩,整张脸瞬间变得煞白如纸——